1949年9月,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先后在中央洛杉磯托兒所、中央軍委保育院(現總政幼兒園前身)和華北軍區招待處工作。1952年復轉地方后到蘇聯專家招待處工作。
為響應“到祖國最需要和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的召喚,選擇了地質作為終身事業,於同年12月20日到剛剛成立不久的地質部工作。報到時,向人事部門提出到野外勘探隊去,不在部機關工作的要求。不久通知他到內蒙大青山地質隊。在53年3月5日出發的當天,又通知他不去內蒙,就留在地質部人事司工作了。在留部機關工作兩年多的時間裡,他先后以書面4次向組織上提出要到野外第一線工作的申請。直到1955年5月批准他到新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305隊(水晶專業隊)去工作。1955年5月16日新婚的第二天,他告別北京、告別父母和新婚的妻子,實現了他做一名勘探隊隊員的理想。在奔赴野外的列車上,寫出:“山高路險頭不回,志在深山心不移,男兒有志志不改,曠野荒涼人不歸”的誓言,這四句話,也成了他的座右銘。就在他到野外隊工作不到半年,隊領導考慮他結婚沒有請婚假,就派他代替採購員要到天津去採購,往返4天路程,再給他10天婚假。到天津后他和愛人商量:領導這樣關心我們,對待我們,我們更要對的起領導,一定要好好的工作。第二天他採購一天,第五天即回到隊上,放棄了組織上批准的休假。
為了實現他獻身地質事業的崇高理想。他堅持做到了“三遷”和“三約”。“三遷”即:三次將北京和天津的戶口主動遷出到野外﹔“三約”即:“婚約”、“相約”和“密約”。“婚約”是:和妻子在結婚前,他向她表明,他要在野外干一輩子,如果結婚,將要長期的分居兩地,如果不同意,就不要結婚。她認為他是一個有志氣、有理想的青年,為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選擇了艱苦的地質事業,並要在野外干一輩子,是一個非常值得敬佩的人,表示要支持他的行動,不僅不扯他的后腿,還要照顧好他的母親,使他安心在野外工作。“相約”是:他到野外工作僅一年半時間,地質部政治部就下令調他到政治部青年部工作。為此,他於1956年10月到地質政治部報道,不想這時接到中央撤銷政治機構的通知,他的工作“擱淺”了。3個月后,經政治部與天津紡織局聯系並同意,將他調到和妻子在一個紡織系統工作。到天津紡織局報第3天,通知他到紡織廠做青年工作。他考慮將聽不到鑽機的隆隆聲,天天要聽到是織布機的噠噠聲﹔又想到在野外工作才一年多就回到了城市,這和我要在野外干一輩和“志在深山心不移”的決心相差太遠了。心裡的不高興被她看出來了,她很嚴肅的對他說,組織上這樣照顧和關心我們,我們要感謝組織,你怎麼成天愁眉苦臉的。他將憋在心裡的話向她吐露出來。她說,這有什麼,你熱愛地質事業,我熱愛紡織工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們都是毛澤東時代的好青年,又都是共青團員,應該把青春獻給祖國。如果你想到地質野外去工作,我還支持你,我們可以在40歲以后,有機會再在一起生活。聽了她的話,他第二天即到紡織局說明了原因,要回了調令重返野外地質隊。“密約”是:1958年在組織上的關懷下,把他調到在天津新組建的地質部物探局北方大隊。(后改為河北省地質局物探大隊)不久這個隊又遷出天津。在離開天津前夕,他和她商定了一個“密約”。這是因為57年他在安徽一個偏僻的地質隊工作時,他們第一個孩子出生12天突發急病,醫院下了“病危通知”。當他接到電報已是第7天了,(因為鄉郵遞員每周送一次信件和電報)。看到電報后,他心急如焚。可一細想,孩子的病已經過了7天,要回去最快也要走4天,如果是不治之病,等不了7天就不在了。於是發回“盡量搶救,路遠回不去”的電報。這件事給她們都留下了難忘。根據這個教訓他倆商定:他在野外有病,她和孩子在天津有病,都不要互相告知,以免去不了和回不來,反而著急。但是一旦得知,那一定是訣別的病,多遠,路多難都要去見上最后一面。
| 下一頁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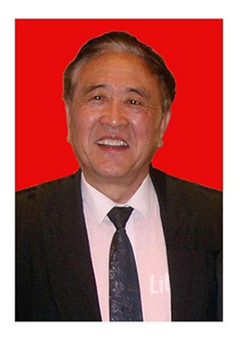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