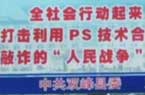“三本賬”支付模式難保障流動人口的獎勵經費
事實上,上述從人口計生部門發放的獨生子女獎勵經費,隻佔獎勵經費的一部分。在多數省份的規定中,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獎勵費分別從相關行政、事業單位經費中列支,企業職工由企業負擔。除此之外的情形,這筆錢才由計生獎勵專項經費支出。
“分類保障”的支付方式,無意間讓人戶分離的阿杰夫婦“躺著中槍”——在戶籍地,他們因在省外有工作而沒法領獎勵﹔在現居住地,法規要求流動人口回戶籍地領錢。
記者發現,這種“三軌制”的保障格局至少存在30年了。
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江立華曾梳理1949年以來的計劃生育獎勵制度。在他的研究中,這項制度經歷了器物支持、物質激勵及福利保障等階段。
其中,器物支持指減免計生手術的相關費用,福利保障則是通過教育、經營、保險等一系列優惠,引導公民響應計生政策。
“為了適應新形勢和新體制發展的需要,以器物支持為核心的獎勵制度,逐漸演變為以經濟刺激為中心的人口規模控制獎勵措施。”江立華撰文稱,物質激勵集中出現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處於獎勵制度的發展階段。
“關於獎勵經費來源,根據我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可實行以下辦法:……”1982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結合當時經濟形勢,設計了一套獨生子女獎勵的保障模式。
與現今“分類保障”的規定類似,該模式保障對象分為國營和城鎮集體企業、機關和學校等行政事業單位、城鎮待業人員三類,前兩者的獎勵經費由本單位承擔,最后一項則從政府計劃生育事業費中開支。
上海市社會科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周海旺告訴記者,現今人口流動的形勢發生了明顯變化。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總體形勢也有較大改善。
機關事業單位、企業、村民或無業者的獨生子女獎勵經費,依然在“三本賬”上﹔而流動人口的獎勵經費保障在“三本賬”之間的角色略顯尷尬。
在2004年全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時任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承認,79%的流動人口需要自己負擔計劃生育手術費,54%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家庭還拿不到獨生子女獎勵費。
“流動人口難以享受法律規定的計劃生育基本服務和相關的獎勵優惠政策。”張維慶說,流入地政府沒有把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經費納入本地財政預算,致使流入育齡人口享受不到免費的計劃生育基本技術服務和有關優惠政策。
周海旺發現,一些企業甚至根本不願意負責本地戶籍人員的獨生子女費。“我們建議,這種情況也由財政統一解決,而不由企業解決。這樣有利於保証獨生子女父母的利益。”
政府答應給的獎勵應當兌現
“如果人口形勢發生了變化,法律卻沒有相應跟上,法與社會就可能會產生一定的脫節。”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教授褚宸舸說,這時應該立新法或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廢止。
褚宸舸認為,流動人口領取獨生子女父母獎勵經費是一個社會問題。目前計劃生育政策為省一級統籌,尚未全國統一,因此公民在本省各地市之間流動,獎勵經費可以在省內“走”。但是,由於各省之間缺乏統籌,這筆經費一出省就沒人負責,形成“兩不管”甚至“三不管”的地帶。
但他同時表示,這一問題並非僅通過修改法律就能解決。“法律的實施必須通過國家機關的權力行為,依靠行政法規、政府規章、地方性法規等一系列規范性文件,一層一層地落實。”褚宸舸說。
在阿杰看來,對獨生子女父母獎勵經費的落實應該對流動人口的特殊情形加以細化。“從技術上來說,人口計生部門應該提高信息化程度,與公安、民政等部門聯網,利用網絡調用個人信息。”他認為,如果能通過電子化平台辦公,沒有必要再讓流動人員為了開個証明來回折騰,負擔不必要的時間、經濟成本。
褚宸舸建議設立財政的轉移支付制度。在他的設想中,可由級別較高的衛生與人口計劃生育部門牽頭,各省賬下有一定金額,不管公民走到哪,均由現居住地賬戶兌現獎勵。比如,福建人到北京,即由北京兌現獎勵,之后就是福建與北京之間的內部走賬問題。
“政府答應給的獎勵應當兌現。政府要帶頭講誠信,既然在法律、法規中承諾了,就相當於政府和公民簽了一個契約,就要給老百姓履行﹔如果違法不作為,也應當承擔行政責任。”褚宸舸強調。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國家人口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馬旭也公開表示,北京將調高獨生子女的補助費用。這句話的背景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北京的獨生子女費一直是每月5元,不過,當年的5元約佔月工資的10%。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到要逐漸完善相應的人口政策,獨生子女補助也是人口政策的一部分。”馬旭接受媒體採訪時表達的這番話,或許會讓公眾對計劃生育政策的不斷完善有了新的期待。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