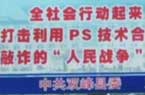“三本账”支付模式难保障流动人口的奖励经费
事实上,上述从人口计生部门发放的独生子女奖励经费,只占奖励经费的一部分。在多数省份的规定中,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费分别从相关行政、事业单位经费中列支,企业职工由企业负担。除此之外的情形,这笔钱才由计生奖励专项经费支出。
“分类保障”的支付方式,无意间让人户分离的阿杰夫妇“躺着中枪”——在户籍地,他们因在省外有工作而没法领奖励;在现居住地,法规要求流动人口回户籍地领钱。
记者发现,这种“三轨制”的保障格局至少存在30年了。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江立华曾梳理1949年以来的计划生育奖励制度。在他的研究中,这项制度经历了器物支持、物质激励及福利保障等阶段。
其中,器物支持指减免计生手术的相关费用,福利保障则是通过教育、经营、保险等一系列优惠,引导公民响应计生政策。
“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体制发展的需要,以器物支持为核心的奖励制度,逐渐演变为以经济刺激为中心的人口规模控制奖励措施。”江立华撰文称,物质激励集中出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处于奖励制度的发展阶段。
“关于奖励经费来源,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可实行以下办法:……”198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结合当时经济形势,设计了一套独生子女奖励的保障模式。
与现今“分类保障”的规定类似,该模式保障对象分为国营和城镇集体企业、机关和学校等行政事业单位、城镇待业人员三类,前两者的奖励经费由本单位承担,最后一项则从政府计划生育事业费中开支。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周海旺告诉记者,现今人口流动的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总体形势也有较大改善。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村民或无业者的独生子女奖励经费,依然在“三本账”上;而流动人口的奖励经费保障在“三本账”之间的角色略显尴尬。
在2004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承认,79%的流动人口需要自己负担计划生育手术费,54%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家庭还拿不到独生子女奖励费。
“流动人口难以享受法律规定的计划生育基本服务和相关的奖励优惠政策。”张维庆说,流入地政府没有把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经费纳入本地财政预算,致使流入育龄人口享受不到免费的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和有关优惠政策。
周海旺发现,一些企业甚至根本不愿意负责本地户籍人员的独生子女费。“我们建议,这种情况也由财政统一解决,而不由企业解决。这样有利于保证独生子女父母的利益。”
政府答应给的奖励应当兑现
“如果人口形势发生了变化,法律却没有相应跟上,法与社会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脱节。”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褚宸舸说,这时应该立新法或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废止。
褚宸舸认为,流动人口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经费是一个社会问题。目前计划生育政策为省一级统筹,尚未全国统一,因此公民在本省各地市之间流动,奖励经费可以在省内“走”。但是,由于各省之间缺乏统筹,这笔经费一出省就没人负责,形成“两不管”甚至“三不管”的地带。
但他同时表示,这一问题并非仅通过修改法律就能解决。“法律的实施必须通过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为,依靠行政法规、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一层一层地落实。”褚宸舸说。
在阿杰看来,对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经费的落实应该对流动人口的特殊情形加以细化。“从技术上来说,人口计生部门应该提高信息化程度,与公安、民政等部门联网,利用网络调用个人信息。”他认为,如果能通过电子化平台办公,没有必要再让流动人员为了开个证明来回折腾,负担不必要的时间、经济成本。
褚宸舸建议设立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他的设想中,可由级别较高的卫生与人口计划生育部门牵头,各省账下有一定金额,不管公民走到哪,均由现居住地账户兑现奖励。比如,福建人到北京,即由北京兑现奖励,之后就是福建与北京之间的内部走账问题。
“政府答应给的奖励应当兑现。政府要带头讲诚信,既然在法律、法规中承诺了,就相当于政府和公民签了一个契约,就要给老百姓履行;如果违法不作为,也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褚宸舸强调。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也公开表示,北京将调高独生子女的补助费用。这句话的背景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的独生子女费一直是每月5元,不过,当年的5元约占月工资的1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要逐渐完善相应的人口政策,独生子女补助也是人口政策的一部分。”马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的这番话,或许会让公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完善有了新的期待。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